新中国摆摊编年史
东方风来满眼春
1992年1月18日下午,时任《深圳特区报》副总编的陈锡添被临时叫到市委,接受了一个特别采访任务。23日晚上,陈锡添风尘仆仆地重新出现在报社和家中,被问及行踪,只字不提。
两个多月后,《深圳特区报》在一版头条,10293字报道了88岁的老人在深圳视察的新闻。紧接着,《羊城晚报》全文摘发,国内主要报纸都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发,新华社也于30日正式播发了该文。《深圳特区报》因此广为人知,作者陈锡添的名字也被印刻在中国新闻史中。
几个月后,在中国的最北方,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一人一早来到了贸易市场。他花一块钱买了门票,又花两块钱租了个摊位,从怀里的布包掏出了全部“家当”:一件夹克、两个饭盒、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、一台小收音机和一罐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。
市长摆摊消息“不胫而走”。电视台的记者来了,工商局来了,群众也来了,众人还不忘帮着市长吆喝:赵市长摆地摊了,大家快来买呀。跟着,警察也来了,说要保护他的安全。
人越围越多,赵市长见好就收,卷起自己的货,回去了。后来他透露,电视台的人其实是他自己找的。但这一场“秀”效果很明显。一时间,整个绥芬河陷入“疯狂”,除了上学的学生,看不到闲着的人,“都在为边贸奔忙”,赵明非甚至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,来方便公务员在业余时间经商。
大家都知道的是,绥芬河市成为第一批边境开放城市。而鲜有人知的是,赵明非是老人的外甥女婿。
老人南巡1年后,1993年11月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更进了一步。这个《决定》第一次明确提出:“一般小型国有企业,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、租赁经营,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,也可以出售给集体和个人。”1993年,私营企业一下子从1990年的9万多户猛涨到23.8万户,增170%。
这年10月25日,南阳市委书记侯玉德也在市场摆摊卖书,引起围观。侯玉德练摊的时间比赵明非要长上不少,而河南也是当时民营经济跑得最快的省份之一。
在许昌,首家职工夜市开办,1.6万平方米的大棚内,机关干部和在职职工利用夜晚时间从事“第二职业”,出售各类产品。省话剧团副团长、省电视台文艺部主任张泽民,离休后和老伴在郑州经三路卖夜餐,下午六点到凌晨两点,生意火爆。
5月,在河南舞阳钢铁厂干了10年的许家印,辞掉“铁饭碗”, 揣着一份三十几页纸的简历,穿行于深圳的各个招聘市场,找到一份业务员的工作。
他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三个月,也不是没有想过先摆个摊平衡开销。后来朋友劝他把简历变薄。这一招果然有用,他很快成为一家叫中达的地产公司的业务员。五年后,他创办了恒大。
合生创展的创始人朱孟依走的路比较“高级”,80年代中期丰顺县城商业刚刚兴起,他看到当地人习惯沿街摆摊,占道经营,这使得整个县城更加嘈杂混乱。于是建设了一个规范的市场,将那些占道经营的摊主全部集中起来,既便于管理,又能够让政府得到稳定的税收,朱孟依得到的回报就是业主的租金分成。从这开始,朱孟依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原始的地产开发商,也正是这次让他挖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。
那个老人在深圳讲的那番话,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,也改变了许多摆摊人的命运。让很多人觉得,世界这么大,应该去看看。当年全国辞职的人,超过了12万。他们很多人都从摆摊开始了自己的路。
这12万也只是冰山一角。有不完全统计,那一年,下海潮之中没辞职但是办“停薪留职”的人则超过了1000万。其中就有那个老人的外甥女婿,当年摆摊的赵市长。
练摊是个技术活
1980年末,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去了趟当地的工商所,领了一个营业执照,编号是10101。字是用毛笔写的。
章华妹的生意,今天看起来寒酸得很。就是在自家门口摆个地摊,卖一些针线、纽扣一类的日用品。
当时,温州的工商局也刚成立。工作人员看到章华妹摆摊,便告诉她,现在做生意放开了,可以去领个证。她回去和爸爸商量,爸爸觉得国家说要改革开放,领了应该不会错。于是,她就去了,拿回来挂在家里。
没成想,这是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,她成了中国第一个合法的个体户。那一年她21岁。
不过,她之后的发展,其实也就一般般。转行做皮鞋失败,足足用了两年时间才处理完库存,不得不重新做回纽扣;她老公做珠宝生意,两个月赔了80万。她儿子自己开酒吧,压根不想跟着她继续卖纽扣。
摆得早不如摆得巧。有几个中年男人,摆摊虽然比她晚,但摆得成功。
1994年,杭州第一家翻译公司——海博翻译社注册。当时公司运营起来很艰难,每个月的公司收入只有200,而房租就要700元。
马云去进地摊产品,鲜花,袜子到义乌去摆地摊,来维持公司的开支,用在这个钱维持了3个月,公司才开始平衡运营。
柳传志也曾在北京中科院的门前摆起了摊,卖的是电子表,后来还批发过旱冰鞋、运动裤衩和家用电器。
本来是中科院人事局的干部,半路出来创业,搞了一家“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”。公司赚不到钱,柳传志不得不练起了摊。这一年,他刚好四十岁。
那个年头,难的不是找工作,难的是摆摊,竞争最激烈的也是摆摊。
马化腾毕业时曾想过在路边摆摊为人组装电脑,但却发现路边摊的竞争很激烈,于是只好老老实实去找工作,在润迅公司一做就是多年。(当年寻呼机时代的龙头老大。)
何帆在《变量》中对这一代人进行过素描:无论50、60、70后,这都是一代人,这都是经历了经济增长的“被挤上车的人”。这一代人穷怕了,时时刻刻会有忧患感,这一代人又是幸运的,他们在赚钱的同时也体会到自我实现的成就感。
这个年代的人们都想活得更好,尤其是草根们。他们硬是靠着街头摊子上的针线、纽扣和电子表,把钱缝在裤子里,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摆摊吧,后浪!
到了80后、90后,摆摊的故事重新被书写。
2008年,23岁的陈昱含在悉尼留学。课余时,就在类似的跳蚤市场摆地摊。作为中南集团创始人陈锦石的女儿,摆摊的动力自然不是因为“贫穷”。
何帆认为,到这一代人,他们追求的是做一些激动人心的事情,他们评判一份工作好不好,会问这个企业好不好玩儿?没意思的工作他们不要,不好玩儿的企业他们不去,他们寻找的是“嗨动力”。
就像陈昱含说的,“通过摆摊这一种独立创业,中南接班人对于商业世界的运行规律,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。”
这些被外界称为“二代”的群体走的是与父辈从“地摊”到企业完全不一样的路径,而更大的新生群体也正在悄悄改变“地摊经济”的传统面貌。
根据《2019中国小店经济温度图谱》,网商银行和支付宝的分析显示,截至2019年,中国小店数量约为1亿,包含网店、街边小店、路边小摊等,带动3亿就业。
其中,日流水3万元以下的各类小店,流水平均增速35%,跑赢GDP;小店图谱显示, 2019 年一半小店凭信用获得贷款支持,做到借钱不求人,99%实现有借有还。虽然店面不大,但信誉却奇高。
作为最早放开地摊经济的城市成都,早在3月,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印发《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》,提出疫情防控期间对商家和经营者实施审慎包容监管政策。
政策推行至今,根据成都市城管委公布的数据,截至5月底,成都市设置临时占道摊点、摊区2230个,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,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,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,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%。
2个多月的时间,仅成都一城就增加了10万人以上的就业,并在两会期间获得总理点赞。
政府和电商大力支持下,资本市场同样闻风而动,与地摊经济相关的个股应声而涨。可提供地摊经营场所的大型商超的茂业商业、百大集团股票飘红,提供货源的小商品城股票上涨。被称为“神车”的五菱荣光推出翼开启售货车,也成为今日网络最热话题。
作为起点的黑龙江绥芬河市28年后因为疫情成为焦点,历史就是这么有趣,将这个并不为人所知的边境城市再次拉回到聚光灯下,而作为应对措施,28年前发生在这座边陲城市的故事也许会在更大范围再度上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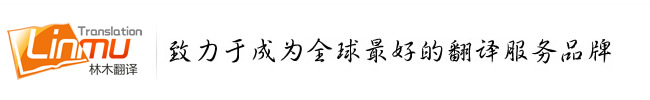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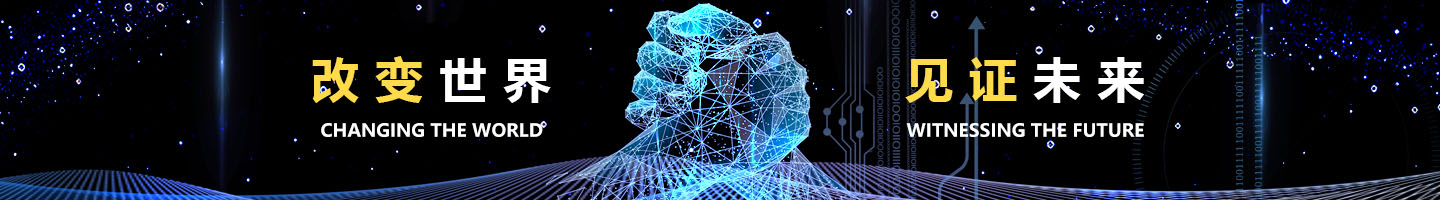
 广州林木翻译服务有限公司
广州林木翻译服务有限公司